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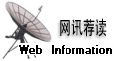 |
元代诗学性情论 |
作者 查洪德 |
资料仅供参考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编辑
他们既然要求诗表现“天理民彝”,则其诗风要求必然是中正平和。王义山在写了上引之《赵文溪诗序》后,意犹未尽,兴亦未尽,又写了《赵文溪诗序性情说》一文,酣畅淋漓地阐发了他的观点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将《诗大序》与《中庸》联系起来解读,将《诗大序》的“发乎情”解释为发乎“中”,认为“吟咏性情”就是“中和”。他说:余读赵侯文溪吟稿自序,首之以吟咏性情。……余尝读《诗大序》,皆自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两句发出来。未发之中,性也;既发之和,情也。《诗》,总言之,则吟咏性情;析言之,则由性而情。《诗》三百,皆情也。情者,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谓也。……人生而静,天地之性也;感于物而动,则情矣。所谓“情动于中”者也。此“中”也,喜怒哀乐未发之“中”,“中”即“情”也①。
这段话的“新意”,就在于将《礼记·乐记》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声”的“中”解释为“中和”之中,于是“情”之一字便等同于“中”既“中和”,顺理成章,《诗大序》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便是“发乎中和,止乎礼义”。他就这样用一个变换概念的方法,完全否定了诗的抒情。这种诗学性情论,无疑是完全背弃诗歌特点,完全否定诗性精神的理论,对诗歌的创作和评论都是极端有害的。他们用这样的眼光审视中国诗史,以往所有的评价都应改写。元人胡炳文就是持此观点评论诗史的,他说:“孔门学诗,致中和也,理性情也;后世学诗,艺焉而已矣。白乐天、刘禹锡下至李益、崔颢,皆负诗名于唐者。《长恨》一歌,亵语诲淫,岂可兴可观者?《看花》二绝,召闹取谤,岂可群可怨者?②”
如此则数千年之中国无诗可言矣。
元人普遍以性情论诗,有不少言论无法归类,但也自有一定价值,也就很难论及。比如元初北方学者郝经,他认为“吟咏性情”就是风雅传统,说:“诗,文之至精者也,所以吟咏性情以为风雅,故摅写襟素,托物寓怀,有言外之意,意外之味,味外之韵。凡喜怒哀乐蕴而不尽发,托于江花野草、风云月露之中,莫非仁义礼智;喜怒哀乐之理,依违而不正,言恣睢而不迫切,若初无与于己,而读之者感叹激发,始知己之有罪焉。”在他看来,“吟咏性情”又有比兴之意,是“托物寓怀”,诗因此而具有唐人所说的“言外之意,意外之味,味外之韵”等特点。诗“吟咏性情”要能感发人意,而这种感发则似乎又是让读者认识“己之有罪”,这可能是对前人关于诗以“理性情”的理解。“诗之所以为诗,所以歌咏性情者,祗视三百篇尔”,下此之诗,时代愈晚则“性情之作”愈衰,而衡量是否为“性情之作”的标准,是是否具有“高古”之风③。他之诗学“性情”论似乎属于一种个人理解。另一学者陈栎关于诗本性情出于人心之天的说法也值得一提,他说:“夫乐由天作者也。所谓天者何也?乐之生原于人心之天,而乐之成协于造化之天也。本于性情则谓之诗,诗实出于人心之天。歌也,声也,皆其发舒而不容已者,而稽之度数则谓之律。律为生气之元,造化生生不穷之天寓焉。由斯而播于音,则乐之生也斯成矣。诗出于心声萌动之天,而律根乎阳气萌动之天,皆自然而然,而非人为之使然,故曰天也。④”
“吟咏性情”原本就是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,元人大多以“性情”论诗,而其诗学理论和主张却各不相同。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,元代诗学“性情”论中基本上听不到“吟咏情性,以风其上”的声音,说明元人基本上没有了以诗干预社会政治的热情,不管是自乐情性、自适情性,还是理性情,不管是性情之真还是性情之正,都基本上属于个体的精神、意趣、意志,其不同只在于或属于感性的,或属于理性的。惟有“性情之正”与社会发生了一些联系,但那只是要以“治世之音,太平之符”去黼黻皇猷而已。诗人社会责任感和治世救民情怀的萎缩,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。(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2期)
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注】
①《稼村类稿》卷十一。
②《云峰集》卷二《明复斋记》。
③《陵川集》卷二十四《与阚彦举论诗书》。
④《定宇集》卷四《论诗歌声音律》。
〔共14頁〕
9
10
11
12
13
14 上一頁 返回第一頁
|